改变人生的决定
7月26日晚上失眠了。当天嗷嗷写到夜里两点半还是不尽兴。写的却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话。
经过一个多星期消化情感、调整心态,终于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这个话题。索性从另一个角度再写。
写这些改变人生的决定。
决定
人生一路,充满决定和选择。小时不懂得取舍,总觉得每一个决定都是天大的事情,每一次抉择都是“改变人生”走向的岔路口。长大后渐渐发现,从比例上讲,普通人的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选择都是无足轻重的。无论再怎么纠结,权衡利弊、患得患失、力争每次局部最优,人生的总体走向却与这些决定毫不相关。殊途同归,既是幸事,也是不幸。
一路走来,生活中有几个重要的决定,让我变成了现在的我。而这些决定的另一面,则一定是境遇迥异、正在面临完全不同问题的另一个我。做出选择的时刻,在从青年走向成年的短暂岁月中纷至沓来,时而应接不暇令人疲于应付,时而伪装得人畜无害,几乎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好在自己不喜欢逞强,在做决定时总会听取别人的意见,结合自己的分析来判断,就算最后结果不尽如人意也并不后悔。当然,也有例外。
他的决定
中学六年同学索思诺,在美国学习生活近7年后,仓促地因疫情回国。
在与他在美国相见的最后几面前夜,我失眠了。此情此景令我感同身受,联想到高考这个人生的岔路口。
2013年我们一同参加高考。他考取了北京理工大学,但入学后并不满意,选择了退学申请美国高校本科。在印第安纳西拉法叶的荒野和寒风中度过了四年,转而来到斯坦福继续研究生。今年他毕业了,在主流留美的风气下,他却有了其他的打算。
当年,他立志去“漂亮国”见识先进文明的模样;走出斯坦福校门,他却戏谑不无颓唐地说,这世道,唉。
在我看来,自己做出本科出国读书的决定的人,一定是有着某种追求或是明确目标的。在北京,虽然当年听说过本科出国这件事,但我所能见到的申请出国的学生,要么是家里有资源有能力的,要么是聪颖过人的牛娃。普通人、海淀教委补习班上见到的众人,总还是主流——在海淀高考竞争,考取国内名校,争取以后找到体面的工作或继续深造。这一两百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将毫不费力地迈进北京的两爿园子、大陆的两间顶级学府读书。那时生活看起来是那么的顺风顺水、理所应当,仿佛在北京读北大才是主流中的主流——毕竟是“北京人大学”!出了社会,见识了沉默的大多数之后,才懂得了幸存者偏差,才逐渐开始明白生活的真相,才开始反思青年时做决定前消息有多么闭塞。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高考前,我的大部分“life changing decision”都做得没啥问题;或者说,与高考相比,所有的之前的决定都是那么无足轻重。家庭条件普通,是典型的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人民”阶级。所以,从小到大,我所接触的,都是真切的、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群众路线思想。就像社会所弘扬的中国梦与撸起袖子加油干精神一样,这种根植于百姓阶层的主体思想,其中一点概括来说,就是“老实本分、勤勤恳恳地努力,就会有收获”。学校教给我们的是这样一种付出和回报线性相关的世界观,因此我的决定也大多基于这样的判断。“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无非是在细节上有所取舍;读书、生活、新知,从小学到中学,无非就是这些内容。
现在想来,在面对高考时,我们这一群人,除了少数家里人有能力帮忙决策者,或是早慧的outlier外,大多是既缺乏对其的了解,也缺乏对其的重视的。
我的决定
实际上,当时我对自己这种缺乏经验和知识有着懵懂的认知,但亦是囿于认知,不知道该如何问出恰当的问题——知道自己不足,但不知道该问谁,面对内行不知道该问什么,是过去在做“重大决定”时的最显著的问题。自己明白,也有所耳闻——高考十分重要。但除了说出几个心仪的大学的名字外,其余一问三不知。道听途说的都是父母的某某同事朋友的孩子去了这个大学读了那个专业,最后出路如何这种极为简略的“因果”式小道消息。也有在大学本科读了两三年的学哥学姐回高中分享经验。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分享的东西颇有些“当局者迷”,有时甚至具有误导性。但若是让真正读完大学本科,甚至本科毕业后几年的“老梆cei”(就像现在这个年纪)给当时懵懂无知的我们讲讲未来的模样,一来很难听懂,二来与学校的理想化的土壤风格不搭、南辕北辙。
为此在大学末尾拍了一点视频,当时也是抱着“抢救性拍摄”的念头去做的。学生生涯只有那么短暂的一瞬,有这样一种“哦原来大学是这样的”的感慨和反思。无论往前还是过后,许多与学校无关、与高考这个决定无关的杂音便会让人无暇顾及读书的意义。
话说回来。为何高考是令我抱憾而无法释怀的“改变人生的决定”,无数次反思后逐渐得出总结。并不(仅)是因为这个决定非自己做出,而更是因为在做这个决定前没能足够重视其“改变人生”的意义,轻视了对手,在“战术”方面投入过多,而“战略”方面调研不足。因此,就算当时侥幸考上了清华,或者真的一根筋去了浙大,我想最终到现在,也一定还会后悔。后悔并非源自结果的好坏,而是对自己剖析不够深入,对对手了解不够透彻,从而“两眼一抹黑”胡乱做决定所造成的。
再说他的决定
或许离开美国去日本的决定,在绵长的人生中无足轻重。但当我们酒杯碰在一起回首时,一定会畅想当初如果选择了另一条路,人生会变成什么样。
这便是失眠的一大原因。亲眼目睹了他无暇思量,仓促做出决定的整个过程。让我回想起2013年报志愿的五天内,自己像无头苍蝇乱撞般志愿填了改、改了填,漫无目的地捞救命稻草般地私信刘佳宸时的场景与心境。虽然索已经有所准备,但这种忽地被外力夺取一种选择的感觉实在不太好。
那些日子,我问了程老师、高老师、678、师队等等人的意见。这些人里却没有真正的内行。虽然高老师说去浙大也挺好,但是现在看来去德国洪堡大学读化工简直就是逆潮流而动。这就好比一个不懂金融和投资的人,上聊闲天儿的论坛如猫扑和虎扑问“各位老哥求推荐几只股票”一样。总有人说对结果,也有人说错结果,可他们的建议的信息熵值几乎为零。
所以,当索说回国去日本时,我三缄其口。因为我知道,在超过自己认知范围的事情上,我给的任何建议都毫无价值,不应影响他做决定。作为对于西方“不评价”精神的个人补充,不让自己的张口乱来给别人添乱,也算是不轻易评价别人的一个方面。
失眠
在做出“改变人生的决定后”,人会经历短暂的犹疑,瞻前顾后,辗转反侧。在岔路口,当自己不得不走向一边时,便会无尽地畅想对岸的风景。
费曼说过,那些将军和政客实在太善于做决定了——他们只需要讨论五分钟,便能决定原子弹丢到哪里。而对于普通人,做一个稍微重要点儿的决定,都会愁得抓耳挠腮。对我而言,中学时能抓耳挠腮的决定,也就是写不完的假期作业怎么混事儿滥竽充数,备受良心煎熬的第一周后说服自己与浪费掉的暑假“断舍离”。算不上改变人生。当然,那时还做了些确实改变了人生的决定,如今反思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至少当时是基于认知的极限做出的,而且确实对人生影响有限。所以逐渐发现,做过的这些决定,对于人生方向的左右,实在微乎其微。
上了大学后,接触到的事物范围更广,也有了更多自己做决定的机会。经历了前述的失败决策,痛定思痛地在接下来的决定后更有效地总结经验。所谓“上道儿”,开窍了。本科到研究生,研究生到工作的两次“life changing moment”,尽管面对的问题的复杂程度并不亚于高考,但由于有了经验积累,做出决定时便更加坦然,终于不会在决定前后长久的心悸。越是这样得心应手,就越会遗憾最初失利时自己没能早些开窍,没能在最需要的年纪拥有这件紫装、甚至恰好遇到好运,从而多走了许多弯路。
好比去美国这件事上,尽管最初走了些弯路,但在做决策前终于和“内行”深入地沟通,在他们的帮助下打开了许多新思路。从此我也深刻地意识到,仅凭自己管中窥豹,容易有失偏颇。只有兼听则明,知道更多事物和观点的存在,才能摒弃一根筋式的狂热。所以,我多羡慕和怀念在高校获得的见到各方样貌、听到各种观点的机会呀。
失眠的原因不仅限于他人被迫做决定时唇亡齿寒的共情,亦在于对于自己现状的反思。在逐渐囿于舒适区后,自己有些抗拒改变,看到关系或近或远的一些人做出重大决定后收获颇丰,不可谓不眼红。
感性和理性在斗争——理性告诉我,我比较满意现状;感性怂恿我,搏一搏摩托变吉普。有一些非常莽撞的热血青年的念头在我心底翻涌,让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内心告诉我,需要重视这些念头,揣度他们产生的原因。提前消费快感又让我肾上腺素飙升,无暇顾及现实,过于理想化。
还有一点隐忧让我在即将入睡时猛地惊醒——
美国不是我的家。
我将不会试图掩藏这个念头。让它生根发芽,并见证它最终将我指向何方。
和心理咨询师Mary的前几次见面,她好意提醒,我似乎处在一种survival mode中。这样的节奏和心态或许会一时使人效率提高,在学业中充满竞争力。但最终会伤害自己(的元气),不应作长久计议。
美国让我感觉到心里上的不适。这种隐隐的阵痛并非来源于物质生活或是工作环境。物质方面,空气清洁、阳光明媚、吃穿用度质量有保障,运动起居便捷而安全,并无任何令人担忧的因素;工作方面,学校的生活改造了我许多缺点和弱点,工作节奏适中,同事人都很好,令我处于充满活力的学习状态中。可以说,美国的生活比我最初想象的还要好,但我依旧能够感觉到心底对于美国的排斥。
-
不尊重人地讲——放眼望去,皆为异族。这种无论是外在样貌,还是内心文明与意识形态都作为“少数”的情况,从小到大还未曾经历过。人是群居动物,而人多力量大这件事从古至今从未改变。作为少数,每每想到遇到事儿时,背后没有自己的“宗族”撑腰,便会底气不足。这会使我倾向于保守、讨好、克己。而无法真正领悟西方的探险精神。
-
利益出发点相悖。我在美国并非为西方普世的福祉效劳;相反,在东西方文化的博弈中,最终的目标还是让自己的文化占据上风。从这个角度讲,我为西方世界出的每一份力,哪怕微乎其微,都与自己的根本目标相悖。这种自己做出了“负贡献”的思想包袱,日积月累也是很可观的负担。
-
疲于奔命。在美国,个人被规则、资本和主流牢牢地控制。作为外国人,一切必须滴水不漏地按部就班地执行,才能保证生活不会“脱轨”。而美国人则乐于见到生活脱轨——这是他们发觉灵感、产生创意的方式。我觉得这种控制扼制了我的创造力,也阻挠了我掌舵自己生活方向、见识到更多不同人的另一个目标的实现。如果过上稳定小康生活的代价是放弃对自己生活的掌控,那我一定无法接受。
暂时而言,美国的工作生活让我看到自己“物质目标”实现的希望。但长久来论,除非美国或自己发生改变,我难以对美国产生认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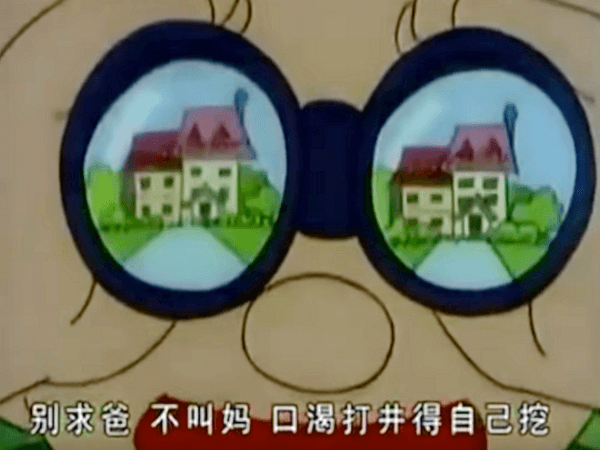
Leave a Comment